奔赴失聯村丨“再艱苦奮斗一次,我家在革命老區”
2023-08-07 05:17:36 來源:新京報
8月3日下午,記者隨門頭溝醫療隊從河北懷來繞道,進入門頭溝“深山三鎮”之一的雁翅鎮。受7月30日強降雨影響,雁翅鎮7月31日斷水斷路斷電,一度失聯,從河北繞過來的醫療隊,是此次山洪過后首次進入鎮里的醫療隊。8月4日清晨,記者隨車從雁翅村出發,大概半個小時左右,抵達了田莊村。
太陽從山坳中慢慢升起,蒸騰的水汽,讓山坳里的村莊更悶熱。在田莊村里,記者看到幾臺挖掘機正在清理村邊的排洪溝,把石頭和泥沙推到路邊,打開通道。有人在收拾四散的垃圾、碎石,清理出來的地方還很少,更多的地方還是一片廢墟,道路上堆滿土石、長長的排洪溝中隨處可見汽車殘骸,電線桿從中間折斷、合抱粗的核桃樹連根拔起……
 (資料圖片僅供參考)
(資料圖片僅供參考)
田莊村是有名的京西紅色村莊,這個京西第一黨支部所在地,剛經歷了一場始料未及的災難,當洪水過后,人們從驚懼中回神,收拾心情,打通被數萬方土石埋沒的道路,重新整理他們付出了無數心血的村莊。“天災沒辦法對抗,再艱苦奮斗一次吧,我家在革命老區,我們這里有這個精神。”田莊村黨支部書記崔春洪嘶啞著嗓子念叨著。
8月4日早晨,雁翅鎮田莊村支書崔春洪(左),在村口組織清理洪水留下的砂石、樹木、車輛。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攝
暴雨再下20分鐘,后果不敢想
見到崔春洪時,他穿著一件志愿者外衣,正在用手勢指揮挖掘機清理道路。
向記者介紹著村里的災情,崔春洪眼淚突然就流了出來。這個一貫硬氣爽朗的漢子哽咽住,背過臉去,指了指旁邊的村委會副書記崔興莊,示意讓老崔繼續說。
洪水之后的晴天,空氣中都是水汽,崔興莊手里拿著一塊毛巾,隔一會兒就擦一次汗。站在排洪溝中,山谷中流出的水已經不再渾濁,清亮見底,水底成堆的砂石,還殘留著洪水肆虐時的狂暴和無情。
就在幾天前,他還從未想過,會遭遇一場超出想象的災難。
田莊村位于南雁路的一處山谷中,地勢較低,緊鄰著排洪溝,村里的老人們,保留著許多暴雨和大洪水的記憶。
“見過這么大的水嗎?”排洪溝里的一塊大石頭上,崔興莊問一位坐著的老人。
“沒見過,1956年的大水,1963年的大水,‘7·21’大水,都沒這么大過。”老人說。
村里的年輕人不多,他們則幾乎沒有和洪水相關的切身感受,門前的排洪溝常年是干的,甚至在地圖上,這里并沒有河,人們更多把它當做一條排洪通道。
房滿霞是田莊村人,她在附近的一處景區上班,景區中有一條瀑布,她過去總覺得,水多了好,尤其在這個干旱山村,水是生機、清涼、美好,甚至還給她帶來了收入。她這次見識到了水狂暴的一面。
崔興莊說,7月29日晚上之前,他們把靠近排洪溝的居民轉到了高處,同時通知全村,把車也開到高處。崔興莊也把自己的一輛農用車,開到了一處兩米多高的高臺上。
暴雨最大的時候,天跟“漏了似的”,持續了20多分鐘,洪水瞬間漲上來了,幾十輛車被沖走,里面還有兩輛挖掘機,崔興莊的一輛農用車也被沖走。后來他在一處公共廁所旁,找到了自家緊貼在墻上、成了一個鐵疙瘩的車。
“再多下20分鐘,后果不敢想。”崔興莊說。
汪洋中的村莊,信號忽然沒了
記者在田莊村看到,村里臨河的一面有一道兩三米高的石墻,擋住了整個排洪溝,村民們的房子地基,和石墻一樣高。
崔興莊站在一處排洪溝被沖毀的地方,對面的一處石墻,被洪水沖開,一處房屋的一角,懸空在石墻的塌陷處。“房子里的人提前轉移了,現在沒回來,也不能回來。”他說。
8月4日,曹興莊告訴記者,在暴雨來臨之前,這里的人被轉移,目前還沒有回來,也不能回來。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攝
一位老人提著一個小桶,從山上下來,走過崔興莊的身邊,踏上一塊被水沖毀的農田,農田里的零星的玉米平躺在泥中,沒有一株殘留,農田一側,一處養雞的圍欄只剩殘骸。
“雞還有嗎?”
“一個都沒了。”
附近原來是一大片農田,洪水過后,幾乎都被埋在砂石下,消失無蹤,面前的一小塊地勢高,在洪流中得以保存,但地里的莊稼和地邊的雞都沒了。
“大樹都沖走了,莊稼能保住嗎?”崔興莊說。
災難發生的時候,崔興莊其實沒想過莊稼,那時候,怎樣保住人,占據了他們所有的精力。
暴雨之前,田莊村里有300多人,包括村民、部分滯留的施工人員,游客則已經提前勸返。崔興莊說,村里常年有游客來,尤其是夏季高峰期,游客很多,他們各自都有交通工具,所以全部提前勸返了。
大洪水到來的時候,崔興莊正不間斷地報告汛情、安排轉移人員的食宿……最緊張和忙碌的時候,電話突然沒有聲音了,一切信號消失。
他想要走出門去查看,可村里路面上全是山上流淌下來的洪水,村道無法通行。
洪水中,中斷的不僅是村莊與外界的通道,村民之間、民居之間也失去聯系,狂風暴雨的聲音、洪水沖進峽谷的咆哮聲充塞天地,踏出房門,風雨立刻把人逼回來。
唯一能互相聯系的電話,也中斷了。
穿過塌方公路,步行去報信
“為了聯系上,啥辦法都想了,能走人的地方,趕緊去查看,不能走人的地方,只能靠喊。”崔興莊對記者說。
在風雨和洪水中,人的聲音如此微弱,緊挨著的兩個院子,都互相聽不到聲音,只能相信提前做好的安排,可以起到作用。
8月1日,雨停了。天上的大水消失,山上流下來的水失去了來源,虛弱了起來。
洪水中困了兩天的人們,開始嘗試著蹚水出門,互相聯絡,打聽消息。
田莊的排洪溝兩側,都是連綿的農田,洪水之后,山上沖下的大石頭、泥沙,淹沒了長長的山谷,大片的農田在洪水中消失無蹤。
南雁路緊靠著山壁,在田莊村東部,和田莊村隔著排洪溝和農田。雨停以后,人們出門查看,才遠遠看到,對面的山上發生了多處坍塌,最大的一處在東北方向,排洪溝的上游,村民們估計,有數萬方土石塌下來,在路面上堆成小山,不僅如此,大部分還傾斜進了排洪溝。
“塌方堵住了排洪溝,洪水積蓄起來,等到沖破阻塞,沖進村里后,力量更大了。”一位村民猜測,沒有這處最大的塌方,洪水的力氣可能沒那么大。
雨停之前,電斷了,隨后,自來水也斷了,洪水的威脅變小,但困難更大了。
想辦法和外界聯系上,是最重要的事情,村支書崔春洪想起來,就在下游不遠處的葦子水村,有一部電臺。葦子水村有一座大壩,盡管大壩中常年沒水,但依然有應急設備,電臺就是其中之一。
崔興莊和崔春洪兩個人,決定步行去葦子水看看,電臺是否還能用,能不能向外界報個信。
走出孤島,重新回到連通的世界中
從田莊到葦子水,沿著南雁路,只有短短3里多,但路上到處都是塌方,路面阻斷,即便步行,也很困難,而且隨處都可能出現新的塌方。但對這個被困了兩天的村莊來說,不論是自救還是求救,首先要得到外面的消息,同時也把村莊的消息傳出去。
3里多路,即便是山路,也不過是二十幾分鐘的路程,但兩個人走了兩個多小時,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尋找通路、預判前方險情上了。
洪災后的村莊,事情千頭萬緒,轉移的群眾,仍要在安置點居住和生活,短時間內還不能回家,以防備新的風險。村里大量的砂石泥土需要清理,物資不夠的,需要在村里就地協調。尤其是水,斷水斷電之后,即便村民們都有存糧,但怎么做飯,是個大問題……
村民向記者講述道,8月2日,洪水變小,村里開始組織人員開始自救,當天晚上,村里的通道逐漸打通,門前南雁路上的堵塞,也被從雁翅鎮一路來的機械,開出了臨時通路,足以供汽車通過。
8月3日,鎮里傳來消息,通往河北懷來的路,在前一天夜里打通了,可以出去報平安了。
崔興莊開車到河北懷來鎮邊城,給在外的村民發消息,告訴他們,村里人都安全。8月3日下午,從南雁路到北京昌平區南口村的路也打通了,田莊村,和這條溝里所有的村莊,有了一條新的通道,盡管手機還是沒有信號,但總算從孤島中走了出來。
記者手記
做好準備,迎接漫長的重建
在8月3日記者進入雁翅鎮時,鎮上通訊仍未恢復,道路僅有一條臨時打通的應急通道,鎮里依靠電臺、衛星電話和外界聯絡,村里則統一收集情況,開車到河北的鎮邊城報平安。對大多數人來說,這樣的聯系其實非常微弱,但至少知道,平安的消息傳出去了。
田莊村是著名的革命老區,早在1932年就建立了村莊黨支部,是京西山區第一個黨支部,也是北京地區第一個抗日民主政權——宛平縣政府的有力支撐點。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,田莊村一直擔任著秘密情報聯絡站的角色,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先烈,用生命傳遞情報。
近年來,這片深山中的熱土,則建設成了遠近聞名的美麗村莊,農業、文旅、研學等產業欣欣向榮。
災難之后,多年發展的心血,在暴雨和洪水中變得七零八落,路邊散落著凌亂破碎的欄桿,為發展旅游而特意選擇的精美路燈躺在泥濘中,田野里的果樹、玉米被連根拔起……
村里的每個人都在忙碌,對他們來說,整理家園的時間還會延續很長時間。隨著時間的推移,在解決物資的來源之前,水和煤氣會越來越少。好在道路打通后,來自外部的支援正在到達,從零星的應急物資開始,越來越多。
即便如此,對田莊村和洪水中所有受災的人們來說,重建也將是一場艱難而漫長的歷程,他們必須堅強起來,在洪水留下的泥濘中重新整理家園。“困難總要一點點解決,破壞掉的,總會重建起來,我們一代代就是這么走過來的。”崔春洪說。
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
編輯 張樹婧 校對 吳興發
最近更新
- 奔赴失聯村丨“再艱苦奮斗一次,我家在革命2023-08-07
- 國羽2金1銀收官!翁泓陽2-1險勝,爆冷世界2023-08-07
- EDG冒泡賽被LNG暴打!Uzi開局7分鐘連死三次2023-08-07
- 油價又有調整2023-08-07
- 黃河大橋護欄“一吹就倒”,需更多調查解釋2023-08-07
- 科迪乳業欠了奶農1.4億元?公司賬面上現金2023-08-07
- 發現沒有,中植系爆雷后的截然不同。2023-08-07
- 80年代的山東章丘,才女李清照的故鄉2023-08-07
- 空x納西妲 神與旅者的逸事102023-08-06
- 室溫超導,真的來了嗎?——一場科學界的“2023-08-06
- “我的青春結束了”!《快樂大本營》停播后2023-08-06
- 重磅新藥獲批!孕產婦死亡“頭號殺手”有了2023-08-06
- 寧德時代回應起訴中創新航侵權專利被宣告無2023-08-06
- 每經操盤必知(周末版)丨華為發布HarmonyO2023-08-06
- 初中孩子英語不好怎么辦(初中英語不好怎么2023-08-06
- IPO企業8月首周撤否率超40%,杜絕“帶病上2023-08-06
- IPO企業8月首周撤否率超40%,杜絕“帶病上2023-08-06
- 一周國際財經|能殺死所有癌瘤的抗癌藥要來2023-08-06
- 俄媒:一油輪在刻赤海峽遭烏軍襲擊受損!受2023-08-06
- 民間救援隊赴涿的三天兩夜:剛下高速就被“2023-08-06
- ESG公募基金周榜31期 | TOP10延續全紅,2023-08-06
- 史上首個!美FDA批準產后抑郁癥口服藥物,2023-08-06
- 一般競爭戰略有三種類型(一般競爭策略包括2023-08-06
- 為什么不用渦軸6造雙發直升機(為什么不用2023-08-06
- 阿水還是Light?EDG雙人路表現低迷,LNG晉2023-08-06
- 那些無理取鬧的家屬,可能得了“天邊孝子綜2023-08-06
- 《城市:天際線》產業區劃分指南攻略2023-08-06
- 京九鐵路線已基本恢復運行 京滬高鐵逐步恢2023-08-06
- 烏克蘭回應“俄大型登陸艦遇襲”:這對俄艦2023-08-06
- 早財經丨烏軍無人艦艇襲擊,重傷俄大型登陸2023-08-0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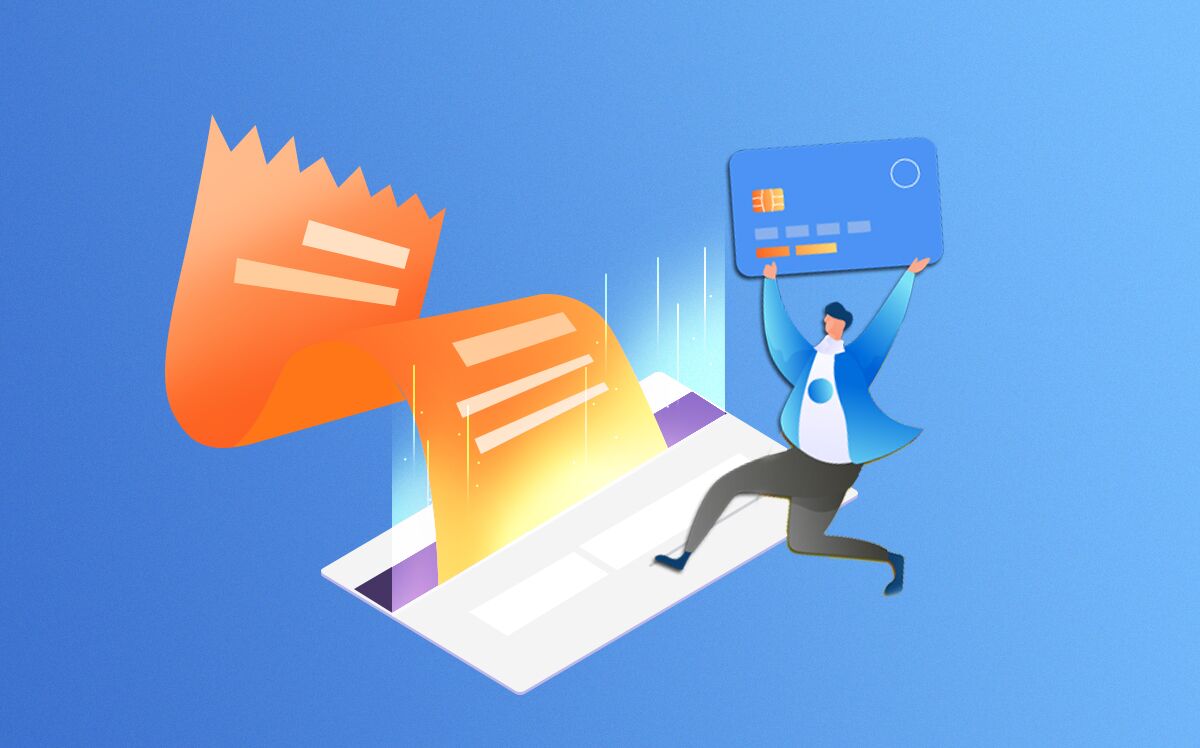






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
營業執照公示信息